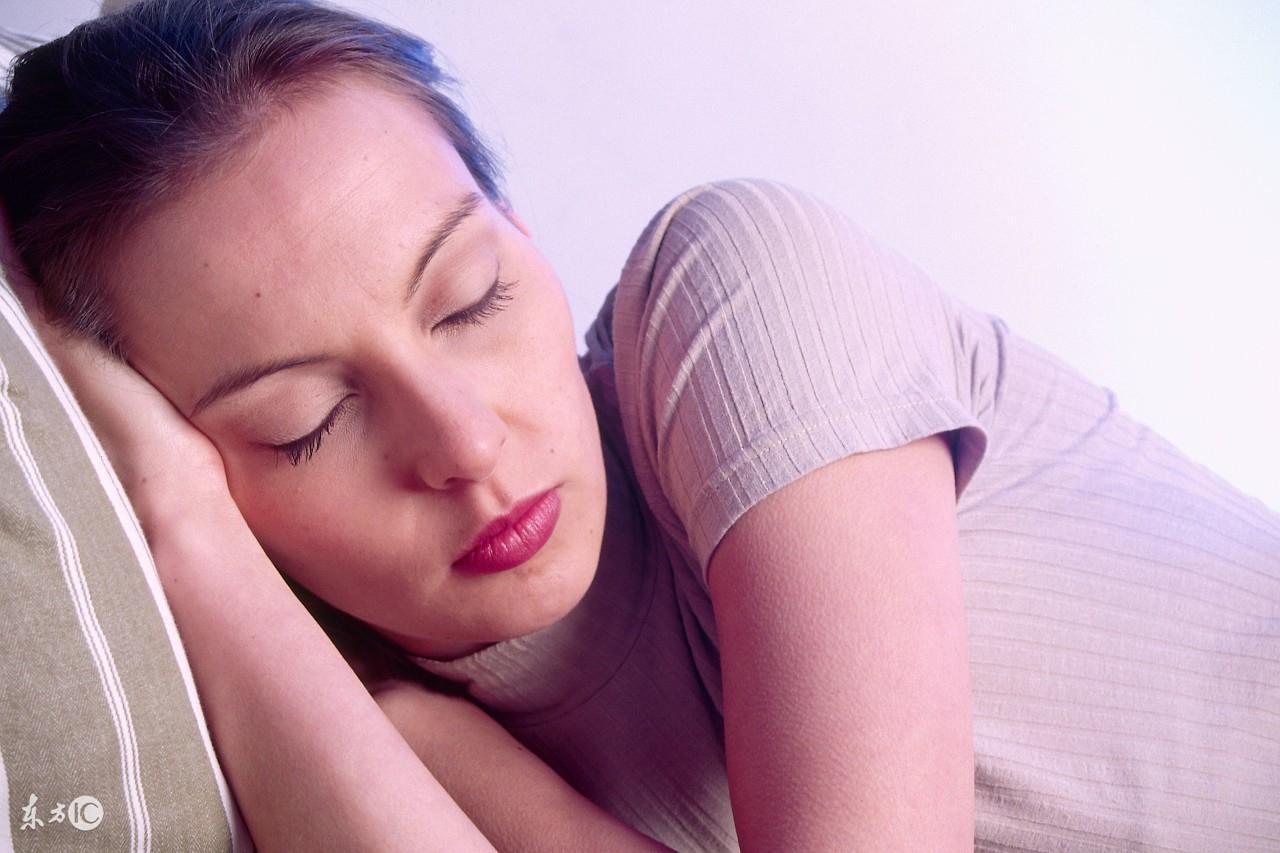民间故事:天、地、人的传说
2025-09-12 01:04:47作者:流年书墨香
民国二十三年秋,冀中平原的玉米秆子黄了梢,风一过哗啦啦响得跟哭丧似的。滹沱河边上有个叫柳树屯的村子,村东头王木匠家正办白事,灵幡在门楼上挂得七扭八歪,像根被雷劈过的老柳条。
"老二家的,你瞅瞅这丧盆子该谁摔?"穿白布衫的老太太拄着枣木拐棍,冲堂屋直吆喝。她左眼生了白翳,看人时总翻着半拉眼皮,活像庙里掉漆的判官像。
里屋传来瓷碗碎裂的脆响,紧接着是女人尖利的哭嚎:"天杀的短命鬼啊!你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咋活哟!"这声音穿云裂石,震得房梁上积了三年的灰簌簌往下掉。
守在灵前的长子王大壮猛地站起来,粗布孝服绷得他肩胛骨直突突。李氏前日夜里吊死在村口老槐树上,脚脖子让井绳勒出紫黑的印子,舌头伸得老长,活像条冻僵的青鱼。
"大壮哥,衙门来人了。"穿灰制服的差役掀开草帘子,后头跟着个戴圆眼镜的年轻人,手里攥着个黑皮本子,封皮上烫着"民政厅"三个金字。
王大壮喉咙里咕噜一声,像是吞了块烧红的炭。上吊前三天,曾攥着半块碎银子往镇上跑,回来时鬓发散乱,鞋帮子上沾着黄泥,直说在河滩上见着个穿红肚兜的娃娃。
"劳驾让让。"戴眼镜的文书挤到棺材前,笔记本哗啦啦翻得直响,"李王氏,四十六岁,本地户籍……"他忽然顿住,鼻尖几乎戳到死者脸上,"这眼珠子……"
众人伸脖子一瞧,俱是倒抽冷气。李氏死不瞑目的双眼不知何时合上了,眼皮底下却渗出两行血泪,在惨白的脸上蜿蜒出两道蚯蚓似的红痕。
"妖孽!定是冲撞了河神!"穿灰布褂子的老汉突然大喊,手里攥着的黄纸钱哗啦啦撒了一地,"前日晌午,我亲眼见她蹲在河神庙后头,跟个穿红肚兜的男娃说话!"
人群炸开了锅,穿花袄的媳妇们交头接耳,说那河神庙早十年前就让大水冲塌了,如今只剩半截石碑立在水洼里,上头刻着"禹王镇水"四个字,被泥巴糊得认不清。

戴眼镜的文书推了推镜架,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黄铜罗盘。罗盘指针滴溜溜乱转,最后直挺挺指向灵堂西北角。众人顺着方向看去,只见供桌上摆着三牲祭品,中间那碗倒头饭上,赫然插着三炷香——本该是两根的。
"三长两短,大凶之兆啊。"文书额角沁出冷汗,笔记本上洇开一团墨渍,"快把香拔了,这香……这香是给活人烧的!"
话音未落,外头突然响起唢呐声,凄凄切切像是送葬的调子。众人冲出门去,只见河滩上影影绰绰走来一队人马,白幡招展,纸钱纷飞,竟是另一支送葬队伍。
"怪了,咱村今儿就老王家办白事啊。"村长眯着老花眼,忽然脸色大变,"领头那棺材……咋是朱漆的?"
按本地规矩,朱漆棺材是横死之人用的。王大壮浑身发冷,想起吊死那夜,村西头刘财主家也亮着灯笼,管家带着人进进出出,搬着几个盖油布的箩筐。
两队丧礼在村口老槐树下狭路相逢,穿朱红寿衣的仵作突然停下,从怀里掏出面铜镜。月光打在镜面上,反射的光斑不偏不倚照在王大壮脸上,烫得他脸颊生疼。
"这位小哥,三更莫走河滩路。"仵作声音尖细,像是用铁片刮瓷碗,"你娘欠的债,该你还了。"
王大壮正要追问,那队伍却突然化作青烟散去,只剩满地纸钱打着旋儿飘进河里。他弯腰捡起一张,纸钱上竟印着个胖娃娃,穿着红肚兜,眉心点着朱砂痣。
"是河神娶亲!"穿灰布褂子的老汉一拍大腿,"早年间发大水,村里献过童男童女,后来有个云游道士说此法有伤天和,才改用纸人……"
话音未落,河面突然炸开一声响,水花溅起三丈高。众人定睛看去,水面浮着个红肚兜,正是李氏死前描述的那件。肚兜上用金线绣着蟠龙纹,龙眼处镶着两颗红宝石,在月光下泛着妖异的光。

文书哆嗦着掏出罗盘,指针疯狂打转,最后直指河心。"底下有铁器……"他话没说完,脚下突然塌陷,整个人栽进河里。王大壮离得最近,伸手去抓却扑了个空,只扯下文书一片衣角。
"救命啊!"文书在水里扑腾,怀里飘出个油纸包。王大壮眼尖,看见纸包上印着"保定府博物馆"的红戳,里头裹着半块青铜残片,刻着饕餮纹,跟村东头老井栏上的纹路一模一样。
河水突然变作墨色,腥臭扑鼻。众人惊恐地发现,文书沉下去的地方泛起血泡,咕嘟咕嘟往上涌,染红了半条河。王大壮正要跳水救人,却被村长死死拽住。
"不能下!"老汉声音都劈了,"这河底下埋着禹王锁龙井,当年大禹治水用九根玄铁链锁住蛟龙,那铁链每六十年一换,算算日子……"
话音未落,河心突然亮起九点幽蓝鬼火,绕着青铜残片盘旋。王大壮想起上吊前夜,曾抱着个铁盒子坐在门槛上数铜板,嘴里念叨着"六十年……该换锁了……"
"大壮!"穿灰制服的差役突然大喊,"你娘棺材底下有东西!"
众人冲回灵堂,七手八脚抬起棺材。底下压着个湿漉漉的木匣,散发着河泥的腥气。王大壮撬开铜锁,里头躺着本泛黄的线装书,封皮上写着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,边角处用朱砂画着河图洛书。
"天有九野,地有九州,山有九塞,泽有九薮……"文书不知何时爬上岸,湿漉漉的眼镜片后射出精光,"这是汉代古本!里头夹着张人皮!"
众人吓得后退三步,只见书页间滑落张薄如蝉翼的人皮,上面密密麻麻刻着经文。王大壮凑近细看,经文最后落款处写着"张道陵"三个小字,正是道教祖师的名讳。
河面突然传来锁链哗啦声,九道玄铁链破水而出,缠住老槐树直往上窜。王大壮怀里的人皮书无风自动,经文化作金芒钻进他眉心。他眼前浮现出奇异景象:先民们抬着青铜鼎在河滩祭祀,鼎中浮着个穿红肚兜的男娃,眉心红痣突然睁开,竟是竖着的蛇瞳!

"是螭吻!"文书惊呼,"龙生九子,螭吻好吞,这孽畜被大禹锁在井底,每六十年要换一次锁链!"
王大壮突然明白过来,那些碎银子,是拿去收买看守锁龙井的更夫。六十年前换锁时,定是出了什么岔子,让螭吻的一缕分魂逃了出来,附在红肚兜上作祟。
河心鬼火突然大盛,化作九条火龙缠住玄铁链。王大壮感觉眉心发烫,人皮经文在血脉中流淌。他抄起供桌上的哭丧棒,蘸着香灰在棺材板上画起符咒。
"天皇皇,地皇皇,河神井底锁蛟龙……"他每念一句,棺材板就亮起一道金光。当最后一道符咒完成,河面突然炸开巨浪,螭吻真身冲天而起,龙角断了一根,鳞片下渗着黑血。
"蝼蚁敢尔!"蛟龙张口欲喷火,却被九道铁链拽得跌回河中。王大壮趁机将人皮书按在铁链接口,经文化作金锁,"咔嗒"一声扣住蛟龙七寸。
东方泛起鱼肚白时,河水渐渐清澈。村民们从河底捞起九根锈迹斑斑的铁链,每根链子上都刻着"永镇山河"四个字。王大壮棺材自动合上,血泪消失不见,遗容安详得像是睡着了。
"大壮哥,你脸上……"穿花袄的媳妇突然指着他额头。王大壮一摸,竟摸到片龙鳞似的硬痂,用香灰一擦,显出个淡淡的螭吻纹。
文书捧着青铜残片直哆嗦:"这是商周时期的祭器,上头刻着……刻着献祭童男童女的记录!"他忽然看向村西头,"刘财主家祖上,怕是当年负责换锁的司仪……"
王大壮想起昨夜看到的箩筐,带着人冲进刘家大院。后院地窖里堆着十二口朱漆棺材,每口棺材里都躺着个穿红肚兜的男娃,眉心点着朱砂痣,皮肤泛着诡异的青白。
"六十年一轮回,用童男童女血祭续命……"村长捶胸顿足,"作孽啊!当年那道士说的没错,这法子有伤天和!"

刘财主被从被窝里揪出来时,还在数金条。看见王大壮眉心的螭吻纹,他突然跪地磕头:"天师饶命!我祖上也是被逼的,那蛟龙说……说若不献祭,就要淹了整个冀中平原!"
王大壮想起《淮南子》里的记载,突然仰天大笑。他抓起把香灰撒在青铜残片上,残片竟自动拼接成完整的河图,露出底下刻着的《禹王锁蛟诀》。
"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"他咬破手指在棺材板上书写,"可人若自甘为刍狗,便真成了蝼蚁。"
当夜,王大壮带着村民拆了河神庙,在井底挖出十二具童男童女的骸骨,每具骸骨脖子上都挂着半块青铜锁。他把人皮书和河图埋在骸骨旁,立了块无字碑。
三年后大旱,滹沱河见了底。村民们在河床上发现个漩涡,深不见底,扔块石头下去,半天才听见回声。王大壮坐在井栏上抽旱烟,烟袋锅子一明一灭,照见他眉心的螭吻纹不知何时变成了禹王鼎上的饕餮纹。
"爹,河底下真有龙吗?"小儿子拽着他衣角问。
王大壮吐出个烟圈,看着它慢慢消散在晨雾里。"有哇。"他指着天边朝霞,"看见没?那红肚兜的娃娃,正在云彩后头冲你笑呢。"
孩子吓得往他怀里钻,却听见父亲胸腔里传来闷雷般的笑声。这笑声惊起一群白鹭,扑棱棱飞过无字碑,在碑顶盘旋三匝,化作九点幽蓝鬼火,倏地钻进地底不见了。
老辈人说,打那以后,柳树屯再没闹过水患。只是每逢六十年一轮回的甲子年,总有人看见个穿灰布衫的后生,半夜坐在老槐树下刻木人。那木人眉心点着朱砂,穿着红肚兜,怀里揣着半块青铜残片,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。
这故事传着传着就变了味,有人说王大壮成了河神,有人说他带着螭吻下地府当判官去了。可每到清明,总有人看见他蹲在无字碑前烧纸钱,火光映得碑文忽明忽暗,仔细听,仿佛能听见锁链拖地的声响,从地底下悠悠传来,又渐渐远去,像是大禹治水时的脚步,一步一步,踏碎了千年的轮回。